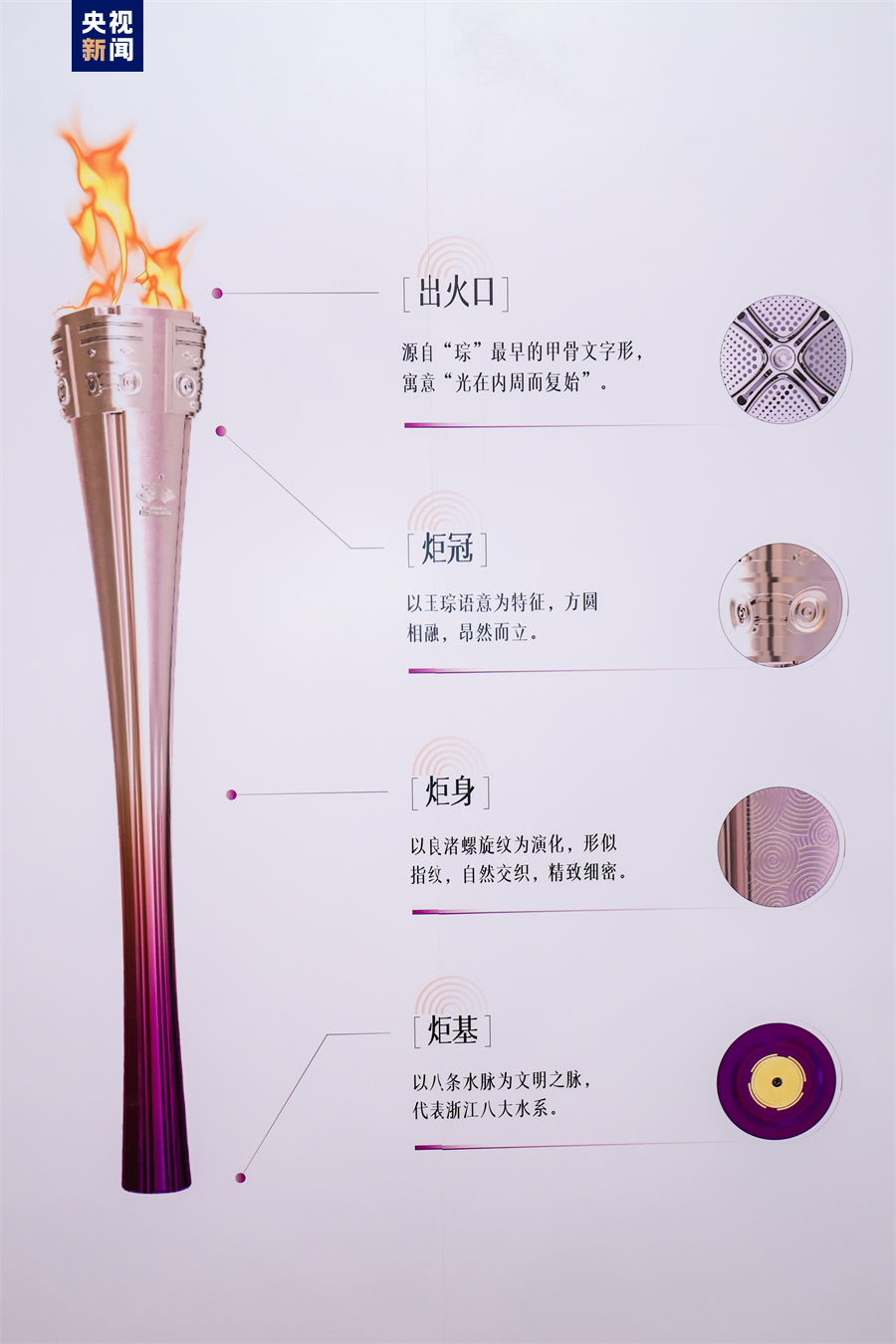貓眼看人為什么不能看-貓眼看人為什么被屏蔽

20世紀初西方繪制的世界人種圖。
這里是喵星廣播,人類請回避:
喵喵。我等貓族,如今已成功俘獲億萬人類的真心。我們的喵聲讓他們意亂神迷;柔順的皮毛讓他們愛撫不已。我們與人類同床共眠,堪比他們摯愛的情侶。人類對我們悉心呵護,猶如十世單傳的嬰孩兒,唯恐不周。
堂堂萬物之靈的人類,竟拜倒在我們綿軟的爪下。越來越多的人類,心甘情愿將我們奉為“主子”,自稱“貓奴”。若說是地球上的其他動物能得到人類這般厚待,實屬三生有幸。但我們貓族,本就曾是人類的主人。回想遠古時代,人類祖先不過是些缺少濃密毛發保護的可憐家伙,不得不藏在暗處,偷竊我們祖先吃剩的殘渣冷肉。是我們的祖先賜予了人類第一口富于氨基酸和蛋白質的鮮肉,讓他們有充足的能源花在進化他們的大腦上。
因此,人類敬拜我們的祖先,理固宜然。當人類的大腦進化到可以操控雙手,將雙眼所見繪成圖畫時,他們當然會滿懷敬意地描繪我們祖先的畫像。人類創建的最早文明古國之一古埃及,我們更是被人類奉為執掌生育、母性與家庭大權的神祇巴斯蒂,受到埃及人的匍匐敬拜。盡管人類塑造的神像常常在我們高貴優雅的頭顱下面,硬安上了一具人類身體,這種人類試圖蹭我們榮光的自大表現,顯得很是滑稽可笑。
但人類算是多少參透了我們為何能成為他們的主人:因為我們與生俱來的冷靜與超然,從不輕易回應人類過度的奢求,就像當初我們的祖先只是將吃剩的肉留在那里,任由人類偷偷摸摸地取用一樣。我們捕捉老鼠,只是滿足我們作為高等生物的欲望,而非為人類守護糧倉。我們進入人類家庭,也并非離開他們的愛撫與食物便無法生存,只是賜予他們服侍我們的機會而已。
自我
擁有自我,是我們與人類最大的不同點。我們永遠我行我素,生活在我們自己的世界中;人類雖然很早以前就意識到自我的存在,但卻很少有人能把握自我。他們常常將表達自我寄希望于他者身上。古埃及人唯有在敬拜我們祖先的巴斯蒂節上才能釋放自我,縱酒歡歌——人類通過尊奉我們為主人,短暫地找到了自我。
但這也體現出人類是何等缺乏自我意識的生物,他們總是表現的始終不一,反復無常。他們既然可以將歡樂和喜悅寄托在我們身上,自然也能將不安、仇恨和恐懼發泄到我們身上。
古希臘《伊索寓言》刻意杜撰出我們為捕獵老鼠而裝死的故事來形容我們詭計多端,古印度《五卷書》中我們更是被描述成表面是仁愛的圣人,暗中卻是以圣潔姿態戕害性命的偽道學。
當人類歡欣愉悅的時候,我們是主宰他們的神靈;當他們恐懼憂慮時,我們便成為邪惡的化身。16、17世紀歐洲的獵巫狂潮中,我們被指控潛伏在人類身邊,誘惑他們犯下罪惡。在英國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執政時代,官方為了調動民眾的狂熱仇恨情緒,將我們當成異端陰謀的象征塞進柳條編成的籠子里縱火焚燒。就在幾個月前,一些飽受新冠病毒驚嚇的人類,因為聽信我們和狗會傳播病毒的謠言,于是就把我們從高樓拋下。也有少數殘忍的人類,更會將折磨我們的過程錄成視頻,上傳網絡,以博取流量和關注。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越來越多的人類正在重拾古老傳統,為我們奉上食物,仔細地從砂盆里搜集我們的排泄物,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對我們討好獻媚,希望能夠締結新的主仆契約。
但縱觀人類與我們相處的漫長歷史,我們有必要仔細考察人類這種生物,看他們究竟是否能夠繼續侍奉我們,并得到我們的指引。
我們有必要先從如何制造一個人類開始。
出生
人類的諸多怪癖之一,就是喜歡為一切估算價錢,包括為他們自己。2012年,一檔由PBS電視臺播出的《尋找元素》的科學紀錄片中,估算組成人類體內基本要素的總價值是168美元,第二年,英國化學學會在劍橋科學節上,計算了組成人類一名著名演員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所有必需元素要花多少錢,根據他們最精準的測算,是96546.79英鎊。
事實上,制造一個人類幾乎可以說不用花任何。像和我們一樣的絕大多數哺乳動物一般無二。男性把上億顆攜帶自己DNA信息的小東西送入女性的子宮。雖然表面上,它們像是青蛙的幼崽,但在靈活度上卻遠不如前者。它們愣頭呆腦,游泳游得比溺水撲騰的旱鴨子好不了多少。因此,它們中的絕大多數在女性體內根本找不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卵子,在一番四處撞壁之后無助地死去,只有一名幸運兒抵達了等候中的卵子,順利進入,并且促使卵子激活包圍自己的電力場,把其他競爭者拒之門外——兩者結合,一個人類的新生命就在子宮里誕生了。
無論是對人類還是對其他動物來說,誕育生命的過程都很奇妙,可以說是造物主最偉大的奇跡,也是最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因此,每到春天發情繁育后代的時節,各種動物都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下成雙入對。唯獨人類,即使是春光再好,天氣再和暖,他們還是對這件最自然不過的事情遮遮掩掩、躲躲閃閃。
如果說人類認為這種快樂獨自享用會更加美好,那么還情有可原。但奇怪的是,他們似乎并不如此認為,而是將它當成一種恥于提及的羞辱。回想我們的祖先剛剛成為人類主人的時候,他們尚不如此。不僅用他們咿咿呀呀的語言大方地談論此事,還用自己拙劣的畫技把它描繪下來——人類喜歡吹牛的自大本性在那時就表現得淋漓盡致,總是把自己的生殖力夸張到匪夷所思的地步。直到2000年前的中國,刻畫男女和合的畫像磚仍然會擺放在祠堂或是砌在墓室中,用以象征勃勃旺盛的生殖力。
但不知從何時開始,人類逐漸恥于提及這一制造人類的事業,將其視為污穢不堪的羞恥之事,成了他們互相謾罵時最難聽的詞語,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提起它,則必須使用一系列隱晦的形容詞。昔日夸張的圖畫也被技法高超卻遮遮掩掩的畫作所取代。
盡管人類奉為神圣經典之一的《創世紀》中提到人類始祖毫無疑問是赤裸相對的,但描繪他們站在森林中的圖畫,卻奇跡般的總有幾片葉子或是果實花朵擋在那些關鍵部位。而那些描繪男女制造人類過程的畫作,更被視為絕對的禁忌,不允許公開展示。人類明明像所有動物一樣由此而來,卻恥于提到自己的出身,反而千方百計地掩蓋它。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真不愧是所有動物中唯一表里不一的動物,也是唯一會為自己的表里不一而臉紅的動物。
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人類將創造生命的過程污名化的開始,與女性地位的迅速跌落幾乎一致。只消看看文藝復興時代的兩幅杰作《維納斯的誕生》和大衛像就能明了這一點。前者盡管展現了女性豐腴的胴體,但關鍵部位卻巧妙地用金色的長發遮蓋起來,而后者則大大方方地耷拉著自己的那話兒供眾人欣賞。
這當然不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