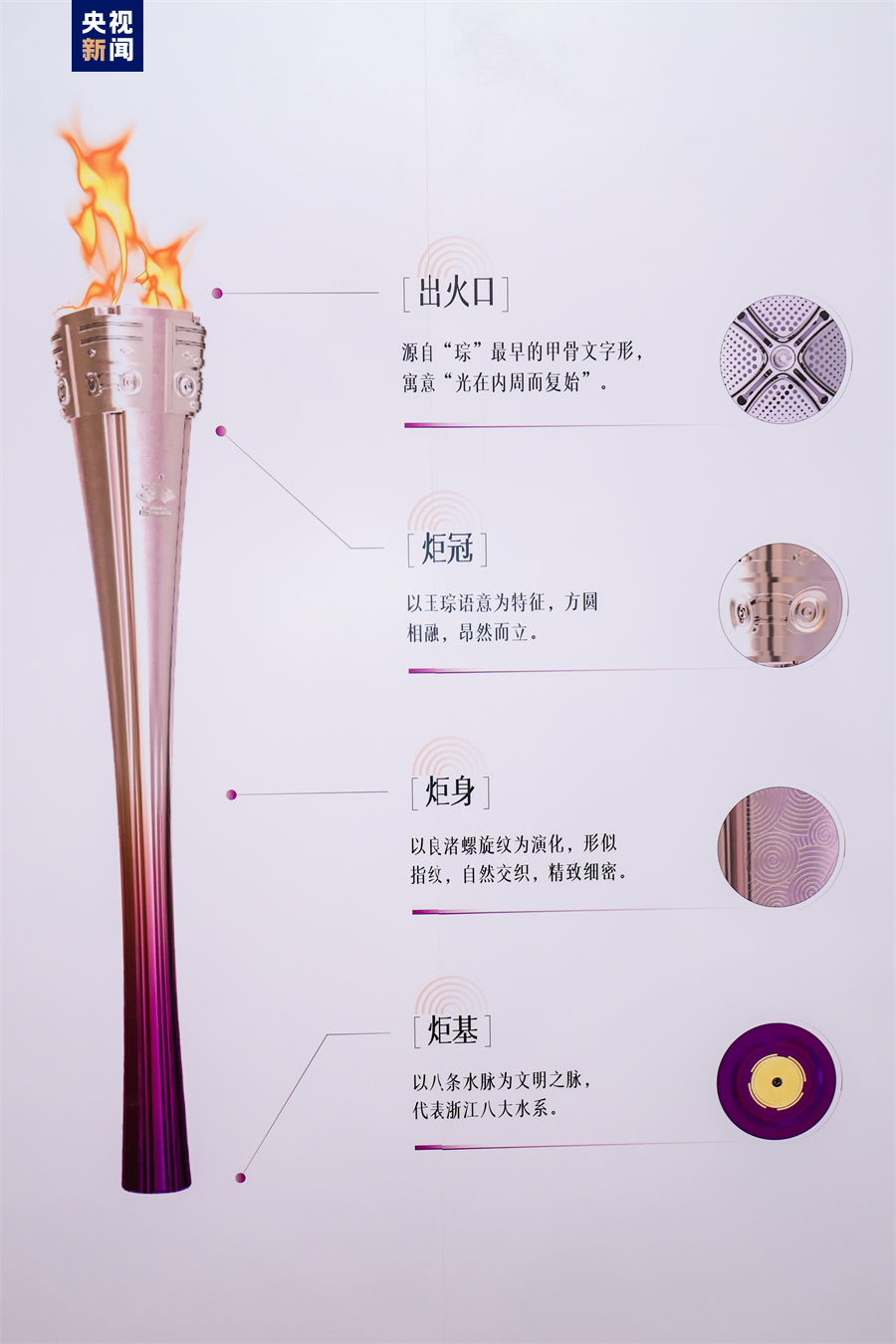以一字結尾的成語(一字結尾成語大全集)
作家的光環掩蓋了卡爾維諾在童話領域的深度研究——在二戰后,卡爾維諾歷時兩年收集、改編了意大利童話。這種研究的動機或許緣起自他青少年時代的精神成長,又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小說創作。

伊塔洛·卡爾維諾(1923-1985)。
關于童話的本質,卡爾維諾這樣闡述道:“對世界的偉大闡釋總是看起來像童話或烏托邦。我們可以說,接受世界本身狀態的作家將是自然主義作家,不接受世界本身狀態但希望對世界進行闡釋并將其改變的作家將是童話作家。”
本文也是新京報小童書系列專欄“寫童書的人”中的一篇。在這個專欄中,我們盡量全面、準確地講述創作者們的人生故事,嘗試探究那些極具原創性的童書,到底是如何從作者的性格、生命體驗中生長出來的。而且我們相信:看見不同的人生,或許能讓我們的心中有更多的活法,不至于被當下的諸多定義、規則束縛。該專欄即將結集成書,敬請期待。
撰文 | 王銘博
在童話《龍與蝴蝶》中,卡爾維諾塑造了一只根本不在意什么金銀財寶的惡龍,它一心只想變成一只蝴蝶——“要是我也能輕盈地停留在花冠上就好了!都說毛毛蟲能變成蝴蝶,可我已經跟毛毛蟲一樣丑了,為什么我還沒有變成一只神奇的蝴蝶呢?”
一個早早開始堅持自己
并接受疏離的男孩
1923年10月15日,伊塔洛·卡爾維諾出生在一個旅居古巴的意大利科學家家庭。他的父親是農學家,母親是植物學家,在卡爾維諾57歲時撰寫的自傳性文字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父母:“我的父母所擁有的知識全集中于蔬菜王國,他們關心著其中的奇跡和特征。而我,被另一種蔬菜——文字——所誘惑,沒能去學會他們的知識。”
在卡爾維諾兩歲時,一家人回到了意大利的小城圣雷莫。在那時,圣雷莫是一個極具包容性的小城,那里長達一個世紀作為各國人種聚居地,住著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小卡爾維諾不喜歡圣雷莫的旅游區,他傾心于大海與森林,無憂無慮地在葡萄園、橄欖樹坡地和崎嶇的山路漫步,來到海邊的高處遠眺。
《樹上的男爵》,作者:[意大利]伊塔洛·卡爾維諾,譯者:吳正儀,譯林出版社,2012年4月。
對高處的喜愛來自童年,也體現在卡爾維諾的創作中。在《樹上的男爵》中,卡爾維諾就用童趣的筆觸講述了在樹上的游戲:“不是像許多孩子那樣圖實惠,他們爬上去只是為了找果子或掏鳥窩,而我們是為了爬樹的樂趣:越過樹干上險惡的蜂巢和樹叉,爬到人上得去的最高處,找舒適的地方坐下來觀看下面的世界……”
高處不僅意味著輕盈與上升,也意味著一種保持距離的抽離。在卡爾維諾的記憶中,他的童年富足、平靜、五彩繽紛,但作為科學家的父母極其嚴厲,小卡爾維諾甚至需要建立一套防御系統來反抗父母帶來的壓力。
但父母作為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和無宗教信仰者的反叛性深深影響了小卡爾維諾。在11歲進入公立中學后,卡爾維諾不參與學習當時普遍必修的宗教課程,成為了學校中的“異類”。但對于卡爾維諾來說,與眾人保持距離并沒有挫傷他的心靈,反而令他早早確立自己人生的一項重要準則:“我不認為這對我有什么損害,反倒讓我習慣于堅持個性,為了正當的理由被人孤立,并且承擔由此帶來的不便,找到正確的路線來維持不被多數人接受的立場。”
《伊塔洛·卡爾維諾:寫小說的人,講故事的人》,作者:[法]讓-保羅·曼加納羅,譯者: 宮林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
這樣的反叛性也是《樹上的男爵》整個故事的起點。十二歲的男孩柯西莫厭惡吃蝸牛,出于對被肢解的蝸牛的同情與對熟蝸牛的味道的反感,他和弟弟將所有蝸牛放生到地窖里。在被父親用鞭子抽打并關進小黑屋后,柯西莫仍舊在飯桌上大喊:“我說過不要,我就是不要!”然后,這個少年轉身跑去花園,爬上了圣櫟樹。
這時候沒人會相信,柯西莫一輩子沒有爬下樹木,他成了樹上的男爵,用常人難以想象的方式在樹上度過了并不遠離世事的一生。
走向寓言與童話的游擊隊少年
1938年9月,、和張伯倫在慕尼黑會面,戰爭隨之而來。15歲的卡爾維諾剛剛開始“對青春、社會、姑娘和書籍有了懵懂的認知”,他的青春期就結束了。“這些使我總抱有一個觀念:在和平與自由中生活是一種脆弱的好運氣,很可能在一瞬間就被奪走。”
從16歲到20歲,卡爾維諾夢想成為一名劇作家,也畫了很多諷刺漫畫,并在一個名叫“小籃筐”的專欄中發表了部分作品,署名杰戈(Jago)。視覺對于卡爾維諾的創作至關重要,在他的童年,漫畫的閱讀遠早于小說的閱讀。他訂閱了《兒童郵報》,花數小時瀏覽漫畫,在腦海中講述這些故事,并用不同的方式詮釋其中的畫面。而更具有創造性的是,卡爾維諾會在切換故事里的敘述主體,想象著在新的故事中,原來的配角變成了主人公。“閱讀這些沒有文字的漫畫,自然而然地培養了我講故事、模仿、構思和想象的能力。”卡爾維諾在《美國講稿》中這樣說道。
《美國講稿》,作者: [意] 伊塔洛·卡爾維諾,譯者: 蕭天佑,譯林出版社,2012年4月。
對視覺的偏好影響了卡爾維諾的文學創作。在談及“祖先三部曲”的創作時,卡爾維諾指出,啟蒙時代童話作家們在寫故事時,腦海里有一個要宣揚的主題,哪怕是具有諷刺意味的童話也是如此,“而我不是這樣。寫這些故事時,我總是以圖像開始,從不是以概念開始。”
不過,卡爾維諾并沒有進入文學院,他先后進入都靈大學農學系和弗洛倫薩皇家大學農業與森林學院學習。但他的興趣并不在“繼承家里的科學傳統”上,于是中途輟學。也是在這個時期,卡爾維諾在壓抑的社會環境中開始嘗試寫作。
1944年,卡爾維諾意識到“最重要的還是行動”,于是和16歲的弟弟一起作為游擊隊員與戰斗。游擊戰就在卡爾維諾少年時隨父親散步的樹林中進行,在那片景色中,青年卡爾維諾“對自己有了進一步的認同和對人類痛苦世界的初發現。”
游擊隊的經歷沒有讓卡爾維諾遭受創傷,反而讓他的精神得以成長。對痛苦世界的勇敢介入,甚至讓卡爾維諾獲得了一種追求快樂的信念,他寫道:“我們要保管的是一種信念,相信生命能夠從零再生,一種公眾對不公的憤怒,還有我們經歷折磨和失敗的能力。但是,我們的重心是勇敢和快樂。”同時,他切身感受到了曾鼓舞萬千游擊隊員的精神,這是一種果斷戰勝危險和困難的態度,同時又混雜著武士的自豪和對此報以自嘲的情感。這樣的對世界與自我的認知,正與日后卡爾維諾對童話的認知相契合:
“童話包含了對這個世界的全面闡釋,丑陋的,美好的,都在里頭,而即便是面對那些最可怕的魔力,我們也總能找到辦法來擺脫它們。”
《通向蜘蛛巢的小徑》,作者:[意]伊塔洛·卡爾維諾,譯者: 王煥寶 王愷冰,譯林出版社,2012年4月。
戰后,卡爾維諾在194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通向蜘蛛巢的小徑》,這本書立刻獲得了里喬內獎,并賣出了當時已算相當成功的六千冊。這是一本講述游擊隊戰爭經歷的小說,主人公皮恩的名字正是童話里的木偶匹諾曹的昵稱。
然而卡爾維諾本人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筆下的童話色彩,直到他的好友切薩雷·帕韋澤指出這一點:“在我渴望建立的新文學思想中,有一個空間,要讓我從小就著迷的所有文學世界復活……這樣,我就開始寫像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那樣的小說,也想寫像史蒂文森《金銀島》那樣的書……帕韋澤第一個向我談起我作品中的童話筆調,在這之前我尚未意識到這一點,從那以后,我開始注意并盡量確認它的定義。”
收集童話的“意大利格林”
1954年,31歲的卡爾維諾開始了他的“意大利童話”收集工作。彼時,他的“祖先三部曲”第一部《分成兩半的子爵》已于1951年出版,并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盡管如此,卡爾維諾還是投身于這份看似與他的小說創作并不相關的作為“意大利格林”的事業之中。
或許得益于兒時的科學家家庭為他帶來的研究者精神,卡爾維諾用兩年時間收集資料、將童話分類并比對不同版本,并從未覺感到枯燥:“我覺得自己的身體里充斥著一種昆蟲學家的熱情……這是一種會迅速轉變為癖好的熱情,為此我寧愿用普魯斯特的全套作品去交換一個《拉金子的驢》的新版本,若是我發現失去記憶的新郎擁抱了母親,而不是那個丑八怪薩拉齊娜,我會失望地發抖。”
《卡爾維諾意大利童話故事:巨人·妙計·龍》,作者: [意]伊塔洛·卡爾維諾 編著,繪者:[意] 法比安·奈格林 等,譯者:彭倩 毛蒙莎,后浪出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21年9月。
卡爾維諾對童話傾注的熱情并非來自對童年、兒時讀物的懷念,而是源自童話與他的人生哲學及美學判斷之間的共通之處。對此,他這樣說道:“對世界的偉大闡釋總是看起來像童話或烏托邦。我們可以說,接受世界本身狀態的作家將是自然主義作家,不接受世界本身狀態但希望對世界進行闡釋并將其改變的作家將是童話作家。”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后,人們普遍陷入意義缺失的境地,卡爾維諾希望尋找到“能夠提供一種精確的道德感,能夠重新提出一種理性樂觀主義的價值觀”的文學形式,這正與他眼中的童話的本質相通。而作為法西斯主義國家戰敗的意大利擁有悠久的童話歷史,這些童話是土地上代代生活的人們的語言,是“一座敘事文學的高峰”,它“從操著不同方言的人民口中崛起”。收集意大利童話讓卡爾維諾覺得自己打開了一個魔法盒子,曾經統治著童話世界的已經遺失的邏輯“重新奪回對這片土地的統治權”。
《論童話》,作者:[意]伊塔洛·卡爾維諾,譯者:黃麗媛,譯林出版社,2018年5月。
或許卡爾維諾是希望意大利重新找回那些曾經人們堅信的質樸的觀念,這些觀念關于命運、勇氣、善惡、友誼,甚至萬事萬物的存在:“在受到魔法支配的相同命運中,也就是在某種復雜而陌生的力量的控制下,仍然盡力尋求自由和解放,猶如一項基本的責任,即使自身難保,也要憑借這樣的努力去拯救他人,在這一過程中也拯救了自己……最重要的是,一切事物的本質是相同的,無論是人類、野獸,還是花草與世間萬物,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具有變化莫測的可能性。”
1956年11月,《意大利童話》出版。次年,“祖先三部曲”中的《樹上的男爵》出版,1959年,《不存在的騎士》問世。談及“祖先三部曲”的創作初衷,卡爾維諾說,他想制定一張當代人類的系譜樹,從對存在的爭取,到對完整存在的向往,再到忠于個體的自決,從而表達一種積極的力量——“它自有樂觀的一面,但‘從不說謊’。”
固執地創造純真
直到成為一種詩意
在作為一位多產的作家的同時,卡爾維諾也是意大利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的編輯,從1955年起,他擔任這家意大利里程碑式的出版社的主管,直到1961年6月為止。在那之后,他成了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的出版顧問。
作為一位才華橫溢的創作者,卡爾維諾非常珍視他的編輯身份。“在出版社工作時,我把更多的時間用在和別人的書打交道上。我不后悔:為群體的文明和睦相處而做的每一件有益的事,都不會是浪費精力。”
保留文學傳統、促進新的作家的誕生是卡爾維諾一直關心的事情。在1968年到1972年間,卡爾維諾還在與朋友們寫信探討創辦文學雜志《阿里巴巴》的可能性。在他的構想中,這本雜志包括相當數量的專欄,通過舉例來闡釋敘事策略、人物類型、閱讀方式、文風體系和詩歌的人類學功能。不過一切要讀起來妙趣橫生。
《馬可瓦爾多》,作者:[意]伊塔洛·卡爾維諾,譯者:馬小漠,譯林出版社,2020年1月。
1963年,卡爾維諾出版了他的另一部極具童話色彩的小說集《馬可瓦爾多》。這部小說集由20個短篇構成,每篇對應一個季節,講述了在城市里生活的貧窮工人馬可瓦爾多的五個四季。在開篇,卡爾維諾這樣描述道:“這個馬可瓦爾多,有著一雙不適很適合城市生活的眼睛:標志牌、紅綠燈、櫥窗、霓虹燈、宣傳畫,那些被設計出來就是為了吸引人注意力的東西,都從來留不住馬克瓦爾多的目光,他看這些東西就好似一眼掃過沙漠里的沙子。然而,樹枝上一片發黃的樹葉,纏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卻從來也逃不過他的眼睛……通過它們,可以發現季節的變化,心里的欲望,自身存在的渺小。”
這是卡爾維諾筆下又一個與抽離于周遭環境的、有趣味的、純真的人。他在灰色的城市的縫隙中發現了蘑菇,暗暗等著雨水讓蘑菇長大帶著全家人去采回加餐,卻在發現清潔工知道有更大的蘑菇時,憤而呼喚所有人來采。人們很開心,有人說:“如果大家中午能一起吃個飯,該多好啊!”然而每個人采了蘑菇后,就各自回家了。
原版《馬可瓦爾多》內文插圖。
卡爾維諾沒有讓故事結束在這里——對于馬可瓦爾多的純真與反抗,卡爾維諾懷著一絲溫和的欣賞與難以抑制的譏笑。采蘑菇的人們很快就見面了,在同一間醫院的病房。不過大家在洗胃后都沒有什么大礙,因為每個人吃到的蘑菇相當有限。
四季輪回,發生在馬可瓦爾多身上的事情雖然都有可笑之處,但卻無法令他改變。他帶著貧窮的家人們去超市假裝購物,體會把商品放進購物車的快感,卻在要結賬時慌不擇路,將一家人帶去了施工的室外腳手架上。他為了在大自然中好好睡一覺,來到公園的長椅,卻一夜未眠。這與法國導演雅克·塔蒂在其電影《玩樂時間》《我的舅舅》中塑造的“于洛先生”有相似之處:不合時宜的人制造著混亂,在城市的迷宮與陷阱中泰然成了一種超然,甚至成就了一種詩意。
《于洛先生的假期》海報。
而這種小人物創造的詩意,會成為城市中的一種奇觀。在另一篇關于馬可瓦爾多的故事中,他執意把公司毫無生命力的植物帶去淋雨水,植物瘋長,竟然像樹一樣高大,已無法再搬進公司。于是馬可瓦爾多換了輛機動小貨車拖著它在街上走,“那植物,在經歷了被大雨拔起的那一番奮力迅猛生長后,現在已經是筋疲力竭了。馬可瓦爾多繼續漫無目的地開著車,甚至沒有發現他身后的樹葉一片片地從深綠色變成了黃色,一種金黃色。”人們跟在他的植物后面,每當一片葉子掉落,就會有好多只手去抓那葉子。
故事是這樣結尾的:“金色的樹葉卻被風揚了起來,飛向那盡頭的彩虹,同樣揚起來的還有那些手和尖叫聲;最后一片葉子也落了下來,它從黃色變成了橘色,接著又變成了紅色、紫色、藍色、綠色,最后又變回了黃色,然后就消失不見了。”
1964年2月,卡爾維諾與阿根廷翻譯奇基塔(Chichita)結婚,1965年5月,女兒喬萬娜(Giovanna)出生。成為父親為卡爾維諾帶來了滿足感,并獲得了一種“意料之外的樂趣”。不久,或許是因為老友維托里尼的去世,43歲的卡爾維諾開始感到自己不再有占據社會生活中心的沖動,“我曾年輕過很長一段時間,也許是太長了,突然我感到自己不得不開始我的老年生活”。但與其說這是一種悲觀心態,不如說是一種直面而上的勇氣:“我甚至希望它早點開始,沒準還可以延續得更長久一些。”
卡爾維諾與妻子、女兒在一起。
在那之后,卡爾維諾與妻子、女兒一起生活,他創作出版了許多具有實驗性的作品,《命運交叉的城堡》《看不見的城市》《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帕洛馬爾》《收藏沙子的旅人》等。
1985年,62歲的卡爾維諾整個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翻譯作品、接受采訪、為1985年至1986年在哈佛大學舉辦的“諾頓講座”準備講稿。
9月6日,卡爾維諾突發中風,18日夜間至19日凌晨,卡爾維諾因腦出血與世長辭。
在他的童話《三個遙遠的島嶼》中,男孩吉羅米諾遇見了一個在沖浪的女孩,他驚嘆道:“你真厲害,竟然能在海浪上保持平衡。”
女孩回答道:“你不能始終對抗海浪,也不能完全被動地跟著海浪走,你必須在與海浪力量的對抗和順應中達到平衡,就是這樣。”
撰文/王銘博
編輯/王銘博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