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課題研究內容、水污染課題研究內容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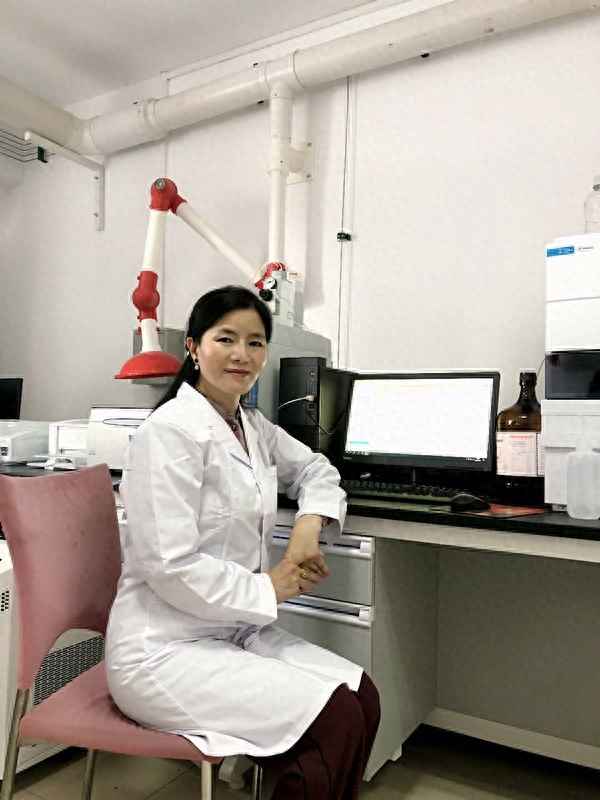
雷曉玲
“誠邀雷曉玲教授為‘水與衛生’培訓班授課,向‘一帶一路’沿線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傳播、推廣中國在水與衛生領域的技術和成功模式……”
2021年1月6日,收到這封來自中國科學院—發展中國家科學院水與環境卓越中心發來的邀請函時,雷曉玲正在實驗室和團隊成員一起逐一核對近日從重慶各處所采水樣檢測數據,更新重慶水質研究數據庫。
作為重慶市科學技術研究院低碳與生態環保研究中心負責人,過去15年,雷曉玲一直奔走在重慶的大山大河間,研究山地水環境變化,解決了50多萬村鎮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疫情期間,她還牽頭編制了全國農污行業首份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和“一帶一路”疫情防控指南,科學指導疫情防控。她先后榮獲“重慶市首席專家工作室領銜專家”、“重慶英才·創新領軍人才”、2019村鎮水環境“中堅力量”等稱號。
讓群眾從“有水喝”到“喝好水”,雷曉玲步履不停。
雷曉玲(中)為學生解疑答惑
結緣·“只有到親水、近水的地方工作,才能知水、治水”
“為何會來重慶?”每個初識的朋友都會問雷曉玲這個問題。
雷曉玲出生于陜西省澄城縣的一個農村,那里常年缺水。在她小時候,父親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前往一公里外的水井挑水,需往返多次才能滿足一家人一天的用水需求。由于長時間挑水,父親的雙肩被扁擔磨出了厚厚的老繭,碰上夏天磨破皮,還會火辣辣地疼。
在雷曉玲的印象里,不僅挑水苦,父親挑回來的水的味道也是又苦又咸。
“全村的飲水源來自河岸邊開挖的一口滲水井,沒有任何凈水設備,喝的時間長了,很不利于村民健康。”回憶過往,雷曉玲皺皺眉頭。彼時,小小年紀的她,有了一個治水的夢想。于是,她在日記本上歪歪扭扭地寫下一句話——我想讓大家喝到好水。
高考后,雷曉玲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填報專業時,她毫不猶豫地選擇就讀環境工程專業,師從清華大學環境系教授張曉健。
學習過程中,雷曉玲跟隨導師多次參與水污染防治課題研究。通過這些研究,也讓雷曉玲更加堅定了治水夢。
從清華大學碩士畢業后,雷曉玲就職于深圳市水務局,8年后又離職前往國外繼續深造,回國后在一家外企水務公司做了一年的部門副經理。
其間,重慶的快速發展讓雷曉玲格外關注,同時,她也發現重慶存在水資源短缺的問題。“重慶雖地處長江上游和三峽庫區腹心地帶,但重慶水資源短缺,不僅僅表現在數量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水的質量上”。
特別是在重慶的一些村鎮,水源復雜多樣,飲水工程規模小且分布分散,管網易受污染,有較大的安全隱患,亟待探索建立適宜重慶山地特征的村鎮集約式供水系統,解決村鎮居民飲水難題。
“我是學水的,只有到親水、近水的地方工作,才能知水、治水。”雷曉玲求學期間掌握的超濾膜凈水技術恰巧能解決這一難題。
2006年,雷曉玲把家安在了重慶,開始了她在重慶的治水之路。
雷曉玲(中)向學生演示試驗過程
破題·“只要能讓群眾喝到干凈水,就值得試試,辦法總比困難多”
此前,超濾膜凈水技術雖具有產業發展前景,但卻因受到超濾膜的性能、生產成本和規模化生產約束,導致其在飲用水處理的應用上并不理想。
在雷曉玲看來,“只要能讓群眾喝到干凈水,就值得試試,辦法總比困難多”。
為了收集前期資料,選好試驗地,雷曉玲和她的團隊花了半年時間跑遍了重慶各個區縣。最終,雷曉玲選擇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龍池鎮展開試驗。
但當地地形復雜,大型實驗設備根本無法搬運過去。
于是,在雷曉玲的帶頭下,團隊成員每天兩頭跑:白天在龍池鎮采集水樣,晚上乘坐火車將水樣拿回位于主城都市區的實驗室進行監測分析,而后又返回龍池鎮。
在雷曉玲眼里,這不算難題,更難的還在后面。
比如,試驗過程中經過超濾膜處理過后的水,檢測出來沒有細菌,但從出水口管道流出來后,細菌又存在了;膜系統在運行了一段時間后,膜組件污染明顯加劇,并出現積泥的情況……
面對困難,雷曉玲和團隊成員沒有退縮,而是選擇迎難而上攻克難題:時刻跟蹤研究原水特性,調整工藝系統設計運行參數,提升膜系統工程安裝施工質量,提高自動化控制系統對膜工藝的融合性等。
眾人拾柴火焰高,經過數百次的試驗,超濾膜集成凈水裝置終于研制成功了!
雷曉玲(前)正在講解試驗
推廣·“我們解決了50多萬村鎮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今后還將更多”
2015年,雷曉玲帶著超濾膜凈水技術參加了綦江區舉辦的“科技改變生活”學術交流會。
交流會上,超濾膜凈水技術以及超濾膜集成凈水裝置引起了當地黨委、政府的關注。
原來,綦江區郭扶鎮高廟村經過旅游開發后,夏季前來避暑的旅客增多,導致當地的飲水問題凸顯。
“當時綦江相關部門負責人聯系到我,希望能幫忙解決高廟村水質超標的問題。”雷曉玲說。
會后,雷曉玲趕到現場調查,癥結很快找到了——當地供水廠工藝較為落后,特別是進入汛期,原有的水處理設施會超負荷運行,導致水質超標。
有了在秀山的治水經驗,雷曉玲信心十足:“超濾膜凈水技術是一種能將溶液進行凈化和分離的膜分離技術,能解決傳統農村飲用水處理技術難以解決的微生物、藻類和濁度等問題。”
技術研究成熟了,但要在海拔1100米的高廟村實際投用,還需要克服設備運輸的難題。
“原來的思路是在工廠里把超濾膜集成凈水裝置安置好,其余設備運輸上來后進行簡易安裝就可以投入運行,看來這個思路不行。”于是,雷曉玲又帶領團隊調整思路,改進技術設備,針對性地開發出“一體化”超濾膜凈水集成裝備。
兩個月后,重慶首個集成化山地村鎮超濾凈水廠和“山地村鎮超濾膜凈水技術應用示范基地”在高廟村建成投用,實現了超濾膜凈水技術從科研到成果的轉化,有效保障了當地兩萬多人喝上安全優質的飲用水。
而后,這項技術在重慶大地落地開花。截至目前,已先后在7個區縣建成示范工程30余座。
“我們解決了50多萬村鎮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今后還將更多。”雷曉玲說,她的治水夢正在實現。
實驗室是雷曉玲最常待的地方
應急·“水在哪里,群眾的需要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污水處理站(廠)等運營單位應加強口罩、手套、護目鏡等防護物資的日常儲備與應急保障……”
進入冬季,雷曉玲帶領團隊奔走各處,宣傳村鎮排水系統運行管理風險防控工作,防范疫情。其間,所運用到的宣傳手冊正是他們在一年前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緊急匯編的防控指南。
“最初大家的普遍認識是新冠病毒是通過飛沫傳播,還沒有提及水污染的問題。但是,我感覺到病毒可能存在從排入口到化糞池、污水管網、污水站(廠)的潛在傳輸與暴露途徑。”雷曉玲敏銳地意識到此事必須重視。
當即,雷曉玲通過視頻連線團隊成員,把編制“全國農污行業疫情防控工作指南”這個決定告知隊員們。
“編制的指南涉及全國,時間緊、任務重。”搭檔魏澤軍覺得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雷曉玲心里也明白,編制這份指南有兩個難關:中國地大物博,各地千差萬別,團隊研究范圍長期在重慶,要把范圍擴大到全國,難;受疫情影響,團隊成員員隔離在家,在溝通不便的情況下,又需短時間內精準地完成編制,難。
“如果不去做,永遠沒有成果。”在雷曉玲的堅持下,這項工作最終還是啟動了。
連續多日,雷曉玲帶領團隊線上收集全國各地城市排水水質采樣數據,聯系全國各地專家、學者匯總關于防控研究的情況,與相關行業、管理部門進行溝通,了解村鎮供排水存在的防控漏洞等。
一個月后,全國農污行業首份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疫情期間村鎮排水系統運行管理風險防控工作指南(試行)》出臺,立即引起社會關注。
與此同時,雷曉玲也應邀為斯里蘭卡、肯尼亞、伊朗等16個國家的相關機構進行在線專題培訓和指導,并主編了“一帶一路”疫情防控指南。
“不少國家發來信息,說我們中國的防控技術走在前面,對他們有很大的指導作用。聽到這些反饋,我感到非常自豪。”雷曉玲說。
如今,雷曉玲的治水腳步不僅在重慶,也廣涉重慶以外的地區,“水在哪里,群眾的需求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雷曉玲仍在不斷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