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xué)生介紹天安城門(介紹天安城門簡短5句)
中軸線是什么?為何要書寫中軸?為何集中寫門?為何用老照片?近日,在北京中軸線上的中國書店雁翅樓店內(nèi)舉辦的《中軸之門》新書分享會(huì)上,該書的作者李哲分享了自己的感悟。在李哲看來,中軸是由建筑群烘托而來,是時(shí)間的延續(xù)和空間的延展,而建筑群之間、建筑群自身,門是樞紐節(jié)點(diǎn)。
在《中軸之門》一書中,李哲循著老照片的蛛絲馬跡,輔以文字的線索,進(jìn)行抽絲剝繭的細(xì)節(jié)探究,將中軸之門的風(fēng)云變幻、趣事逸聞、謎團(tuán)考證一一呈現(xiàn),同時(shí)也分“門”別類,深入解讀,將中軸那些鮮為人知的細(xì)節(jié)娓娓道來。本期的京華物語,就選擇了其中關(guān)于“匾額之謎”的部分,一起來聊聊過去北京城門上的匾額。
以下內(nèi)容節(jié)選自《中軸之門》,標(biāo)題為摘編者所加,非原文標(biāo)題。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由出版方授權(quán)刊發(f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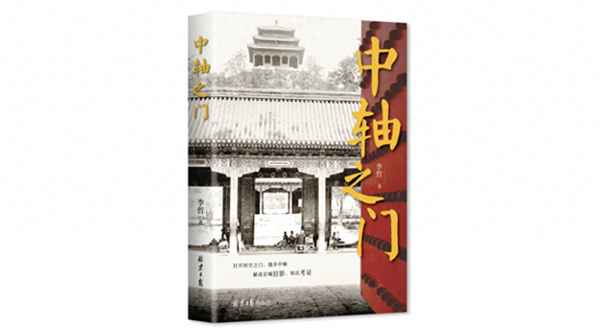
《中軸之門》,李哲 著,北京日報(bào)出版社,2023年5月。
城門上的匾額
1915年底,全城換城門滿漢雙文石匾為漢文石匾,由書法家邵章題寫。據(jù)《燕都叢考》:“各城門額,從前皆并書滿漢文。民國紀(jì)元,以漢文石額易之。時(shí)貴陽朱桂莘長內(nèi)務(wù),以屬邵君伯炯章,伯炯書成,頗自許,朱公付諸庸工刻石,邵君怒,馳書索回,朱公遜謝,改用良工乃已,今日各門之額,皆邵君之書也。”
宣武門匾額如今藏于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館。筆者還在北京市規(guī)劃展覽館看到了明代阜成門匾額,平則門明初石額亦藏于此。
宣武門滿漢雙文匾額(《中軸之門》內(nèi)頁插圖)。
永定門石額和城樓清代木匾均藏于首都博物館。當(dāng)年很多匾額拆除后,暫存在內(nèi)城西南角樓內(nèi)的市政工程處太平湖倉庫,可能時(shí)光流轉(zhuǎn),很多也就散落了。除了正陽門的石匾還在原處,筆者只在德勝門箭樓上見過展覽的德勝門石匾,大清門的滿漢雙文匾在故宮收藏未展出。此外,至今未見到滿漢雙文石匾留存。
阜成門民國漢文匾額(《中軸之門》內(nèi)頁插圖)。
五牌樓的“正陽橋”匾額
八國聯(lián)軍入城時(shí),五牌樓的“正陽橋”匾額還在,不久后的1900年夏或秋,匾額丟失,空心了,后來在修繕時(shí)又補(bǔ)上了,修繕記錄明確說“正陽牌樓一座,欠中心匾一方”。庚子年之前,前門大街五牌樓(正陽橋牌樓)上的匾額,是滿文在右,漢文在左,這在《乾隆南巡圖》里可以看到。修繕后的新匾額變成了滿文在左。
《乾隆南巡圖·啟蹕京師》里的五牌樓,滿文在右,漢文在左(《中軸之門》內(nèi)頁插圖)。
這牌樓的修繕遠(yuǎn)早于前門樓子。清末民初,可清晰看到正陽門箭樓匾額依然滿文在右,而正陽橋牌樓匾額則滿文在左,不再是以往的和諧,而是有點(diǎn)滿擰。
正陽門箭樓滿漢雙文石額(《中軸之門》內(nèi)頁插圖)。
為何會(huì)有這樣的次序變化?有人說庚子國變后大清氣數(shù)盡了,連正陽橋牌樓匾額都改為漢文在前了,這基本是臆想,到清帝遜位,規(guī)矩也沒亂過,牌樓匾額也是朝廷修繕時(shí)自己換的。
有觀點(diǎn)則認(rèn)為,橋牌樓匾額一律滿文在右,街牌樓匾額一律滿文在左,這是當(dāng)年為迎鑾而倉促中整成了街牌樓匾額。的確,四牌樓這類街牌樓匾額皆是滿文在左。
清初故宮和皇家壇廟滿漢文匾皆滿文在左。因書滿文順序是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左為上。乾隆年間改,滿文雖以左為尊,但仍要按漢文順序置于漢文之上(右),午門到神武門皆滿右漢左。沈陽故宮仍存滿左漢右。
那么正陽橋牌樓匾額也可能是乾隆時(shí)改的,改為滿右漢左。有可能乾隆年之前,正陽橋牌樓就是按清初老規(guī)矩滿文在左的。即使有《乾隆南巡圖》為驗(yàn)證,也不排除這種可能。
匾額消失(《中軸之門》內(nèi)頁插圖)。
如果是這樣,其實(shí)是有兩種可能性的。一種是倉促中按街牌樓更換了匾額,即重新制作;另一種可能是重修時(shí),翻出乾隆年前老匾,重新用上。也就又成了滿文在左,漢文在右,同清初一樣了。
1906年之前的崇文門城樓(《中軸之門》內(nèi)頁插圖)。
到了民國,就沒有滿文了,連漢文也重寫了。
“使天下平安的門”
清朝入關(guān)以后,把明代的承天之門,改為天安之門,應(yīng)是順治八年(1651年)重修時(shí)改名換匾。匾額上書“天安之門”,有滿蒙漢三種字體,應(yīng)是和順治十年(1653年)的慈寧宮匾額同樣,從右至左,滿蒙漢依序排列。漢文采用了篆書,這樣拉長字體與另外兩種字體協(xié)調(diào)。滿文采取了意譯,意思是“使天下平安的門”。
之后取消三體文字,改為兩種字體的天安門匾額后,上邊的字跡印痕也在。去掉了蒙文,也去掉了“之”字,采用了楷體書“天安門”,比篆書字體更顯莊重大氣。清帝遜位之后,1915年底,內(nèi)外城門、皇城門及故宮前朝匾額均由滿漢雙文匾改為漢文匾,“天安門”三個(gè)大字居中書寫。
1950年勞動(dòng)節(jié),天安門的舊匾額還在。1950年國慶節(jié)前為安放國徽,挪走了匾額。1950年國慶時(shí)國徽已經(jīng)安放,匾額此時(shí)應(yīng)該已經(jīng)挪到了后面。后來,這個(gè)匾額于1982年在一個(gè)木廠被發(fā)現(xiàn),銅字已經(jīng)沒了,可以看到匾額上有字痕,還看得非常清楚,字痕顯示為“天安之門”,也就說明這塊匾額應(yīng)是清初做的匾額,清代的天安門匾額和民國時(shí)期漢文匾額,其實(shí)是同一塊。
掛的是青石匾額,還是木匾?
神武門直到1924年都還是清皇室掌管,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掛了李石曾(李煜瀛)題的木匾。后來換了石匾。1971年換了如今的,郭沫若題寫,水泥邊框,近年也進(jìn)行過修繕。
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掛了李石曾題的木匾(《中軸之門》內(nèi)頁插圖)。
單士元先生在其《庭訓(xùn)閑話瑣記——我與初創(chuàng)時(shí)期的故宮博物院》一文中,描述了民國時(shí)故宮博物院匾額的書寫細(xì)節(jié)以及成立典禮實(shí)況。
這榜書匾額是由李石曾所寫,他是兩代帝師李鴻藻之子,也是清室善后委員會(huì)委員長和故宮博物院理事長。善榜書,功力極深,這匾額是他在故宮文書科內(nèi),粘連丈余黃毛邊紙鋪于地上,用大抓筆半跪著書寫的。單士元先生當(dāng)時(shí)捧硯在側(cè)。
但典禮當(dāng)日,到底掛的是青石匾額,還是木匾,卻說法不一。據(jù)單士元先生記述:1925年10月10日,舉行典禮,當(dāng)日神武門外搭起花牌樓,門洞上鑲嵌著李石曾先生手書顏體大字“故宮博物院”青石匾額。但另一種說法是:木匾才是建院原裝,青石匾額是1930年換上的,上款則是“民國十四年雙十節(jié)”,下款“李煜瀛題”。
故宮博物院更換為青石匾額(《中軸之門》內(nèi)頁插圖)。
木匾和石匾都有舊照,如果是如單先生所說,那就要探究木匾何時(shí)存在,從邏輯上看,第二種說法更合理。
原文作者/李哲
摘編/何也
編輯/羅東
導(dǎo)語部分校對/柳寶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