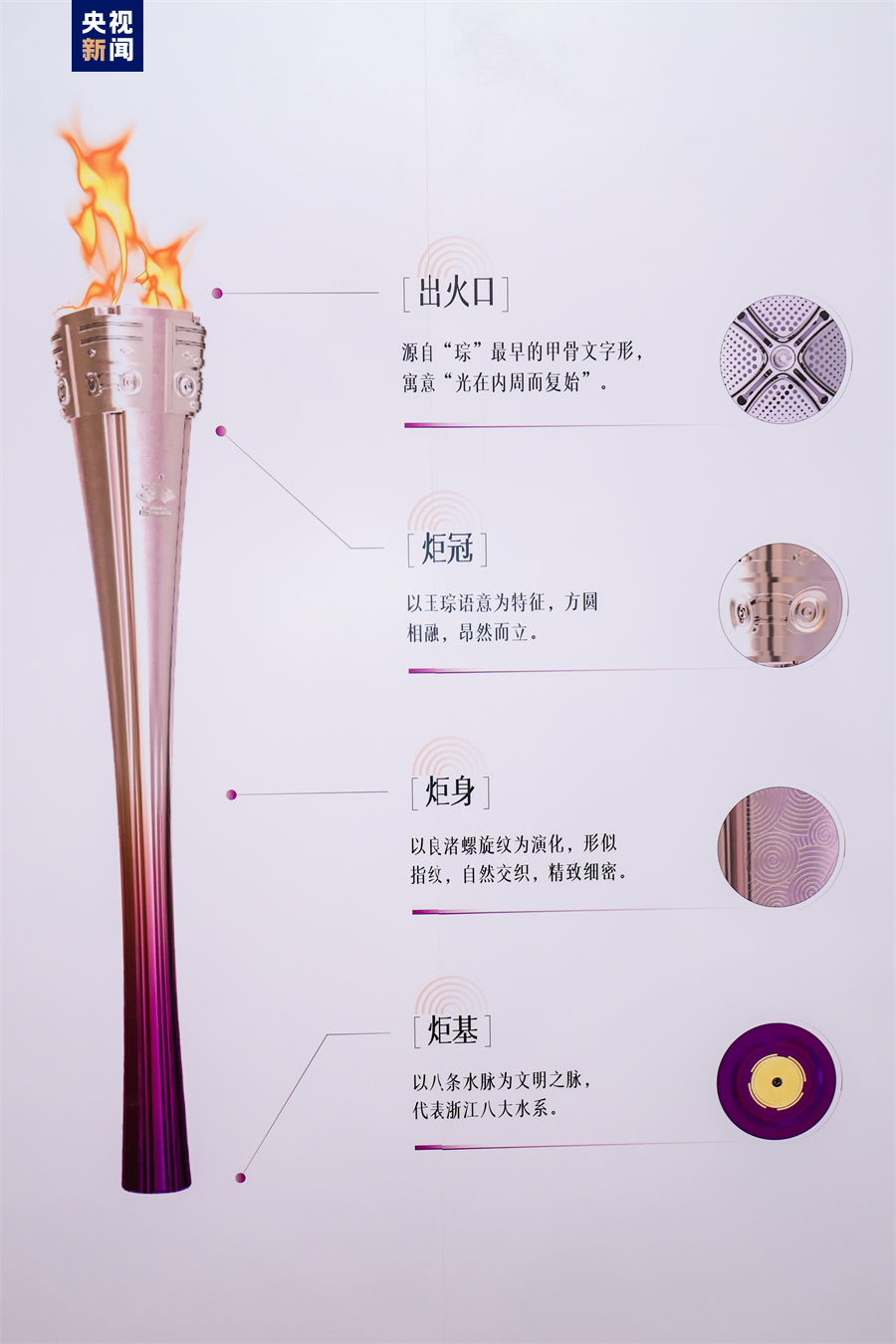獨闖非洲馬拉維小助理(獨闖非洲馬拉維小助理結局)

H. 賴德·哈格德
這個故事是我的老朋友艾倫·夸特梅因親口告訴我的,在南非的時候我們都叫他“獵手”夸特梅因。他在約克郡買了一所房子,有一次我到他家里逗留做客,就在某一天晚上閑聊時聽到了這個故事。不久之后,他唯一的兒子死了,這給了他沉重的打擊,他隨即離開了英格蘭,與他同行的還有兩個老朋友——亨利·柯蒂斯爵士和古德上尉——他們都是他昔日的航海伙伴。自此他就完全消失在非洲大陸黑暗的心臟地帶了。他一直以來都聽到一些傳言,說是在廣袤無垠、人跡未至的非洲內陸高地上,生活著一個白種民族——這一次他終于被說服,把在有生之年尋找到他們當作自己的抱負。懷著這份狂熱的追求,他與同伴們啟程了,對此我幾乎可以斷定,他們再也不會回來。我只收到過這位老紳士的一封信,是遠自非洲東海岸塔納河上游的一個哨站發來的,在桑給巴爾島[1]以北大約300英里處。信里面說他們經歷了許多艱難險阻,但都安然無恙;信中還說,他們已經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這使他信心百倍,堅信他們執著的尋蹤之旅將會是一次“宏偉而又史無前例的發現”。然而,我很擔心他所發現的是死亡;因為這封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從那以后,再沒有人聽到過這支探險隊的任何消息。他們似乎完全消失了。
那是我在他家待的最后一晚,他把下面的故事告訴了我和前來吃飯的古德上尉。他已經吃完了晚餐,為了幫我和古德把第二瓶酒喝完,他也喝了兩三杯陳年波爾圖葡萄酒。這對他來說是非同尋常的,因為他飲酒一向節制,過去還常常說,他在殖民地居民中生活了很多年,親眼目睹了酗酒對殖民階級——者、運貨騎手等等——的影響,也因此對酗酒感到恐懼。正因為這樣,幾杯美酒便在他身上發揮了更大的效力,讓他布滿皺紋的面頰泛起一絲紅暈,也讓他比平時更加健談。
多么可愛的一個老頭兒啊!我的眼前浮現出他的形象,一瘸一拐地在門廳踱來踱去,灰白的頭發豎起來像硬毛刷一樣,一張皺巴巴的黃臉,黑色的大眼睛如老鷹般銳利,又像公鹿般溫順。整個房間都掛著他無數次遠征的戰利品,每件戰利品都有個故事,他要是有時間能一一講述那該有多好啊。在平常他不會那么做,因為他不太愿意講述自己的冒險經歷,但是今晚這瓶波爾圖酒讓他打開了話匣子。
“啊!你這個畜生!”他一邊喊道,一邊在一個大得出奇的獅子頭骨下停了下來。這個頭骨固定在壁爐架上,頭骨的上方是一長排的槍,獅子的下頜張到最大。“啊,你這個畜生!過去12年你給我添了多少麻煩,我猜,要到我死的那天你才會罷休吧。”
“夸特梅因,把那個故事告訴我們吧。”古德說,“你常答應了我要講,但到頭來一直都沒有。”
“你最好別讓我講。”夸特梅因說,“這故事有點長。”
“講吧。”我說,“時間還早,而且我們還有些葡萄酒沒喝完。”
就這樣,經過我們的一番懇求后,夸特梅因從一直放在壁爐架上的一罐粗制布爾中拿了些出來填滿煙斗,仍然在房間里踱來踱去地開始了他的故事:
“我記得,那是一八六九年的三月,我在西庫庫尼[2]國內。當時正值老國王西夸提病亡,西庫庫尼掌握了大權——我忘記他是用什么辦法得到政權的了。不管怎樣,我當時就在那里。我聽說巴佩迪人從非洲腹地運來了一批數量巨大的象牙,于是我趕了一輛載滿貨物的四輪牛車從米德爾堡[3]出發,想用這批貨換到部分的象牙。這么早的月份就進入這個地區是有些冒險的,因為正是熱癥流行的時候;但我知道還有幾個人在打這批象牙的主意,于是我決定碰碰運氣。長期漂泊在外讓我耐苦耐勞,所以一路上我幾乎都沒有停過車。嗯,開始的一段路程還是挺順的。那是一片稀樹草原,景色很美,連綿的山脈跨越平原,圓形的花崗巖丘陵四處聳立,像哨兵一樣注視著起伏的低矮叢林。但是天氣極其炎熱,熱得像一口蒸鍋。我是三月份到的那里,當時正值非洲這個地區的秋天,空氣里都彌漫著熱癥的味道。我沿著象河[4]往南趕路的時候,每天清晨都會鉆出牛車,四下張望一番。根本看不到什么河,只有一條長長的白浪,像是被干草杈輕輕拋起的細軟棉絮。那就是熱癥的瘴氣。灌木叢中也騰起蒸汽形成的小漩渦,似乎有成百上千個小火苗在燃燒——千萬噸腐朽植被散發出臭氣。那里的景色真美,卻是死亡之美;所有這些水汽生成的線和點共同在這片大地上書寫著一個詞語——‘瘟熱’。
“那一年疫病流行,人心惶惶。我記得,我來到了疙瘩鼻部族[5]的一個小村莊,于是就跑去看看能不能弄到些酪乳和玉米。走近的時候,我突然發覺這地方一點聲響都沒有。沒有小孩子的吵鬧,也沒有狗的吠叫。看不到當地的山羊和牲口。這地方顯然沒多久之前還有人居住,現在卻靜得跟周圍的灌木叢一樣,只有幾只珍珠雞飛出村子柵欄門旁遍布密刺的梨樹叢。我記得,進去之前我猶豫了一下,那里所有的一切彌漫著荒涼的氣息。人類沒有侵擾過的地方,大自然便不會顯得那么荒涼,她只會顯得迷人;可是一旦人類到了這里,又離棄了這地方,她就會變得荒涼。
“我進了村子,向主屋走去。屋門前,一張很舊的羊皮地毯蓋著什么東西。我彎下腰拉開那條毯子,接著大吃一驚地縮了回去,原來毯子下面是一個死去不久的年輕女人的尸體。有那么一刻我想掉頭就走,但是好奇心驅使我跨過那具尸體,然后手腳并用地爬進了小屋。屋子里暗得看不見任何東西,但是我能聞到各種氣味。我點了根火柴。這根火柴緩慢、微弱地燃燒著。隨著火光漸亮,我看到周圍是一家子沉睡的男男女女和小孩子。這時火柴突然明亮地燃燒起來,我這才看到他們也都早就死了,一共有五個人,其中一個是嬰兒。驚慌之中火柴掉到了地上,我只管朝著屋外摸索,這時我瞥見角落里有一雙明亮的眼睛。我以為那是只野貓或者其他什么動物,就再次加快了步伐。突然那里傳來了聲音,先是喃喃自語,接著是一連串可怕的呼喊聲。我匆忙點燃了另一根火柴,看清楚那是一雙老太太的眼睛,她裹在一件油膩的皮革衣裳里。想到她可能沒辦法或者不愿意自己出來,加上那股惡臭也讓我無法忍受,我拉著她的胳膊,將她拽出了屋子。她看上去骨瘦如柴,全身裹著黑乎乎、皺巴巴的羊皮。唯一的白色就是那些羊毛,如果不是她的眼睛和聲音,她看上去完全就是個死人。她以為我是來把她帶走的魔鬼,因此才那樣大聲呼喊。我把她帶到貨車旁,給了她少許的南非白蘭地,接著又煮了一品脫肉汁讓她灌下,這是用前一天獵到的一只藍角馬的肉做的。喝了這些之后,她的氣色立刻好了許多。她能說祖魯語——原來她是恰卡[6]時期從祖魯領地逃出來的——她告訴我說,我看到的所有人都死于瘟熱。他們死了以后,其他村民就搶走牲口,逃離了村子,留下這個年老體弱、生活不能自理的窮苦老婦人。要不是遇到我,她肯定不是要餓死就是病死了。我找到她的時候,她已經在那堆尸體中坐了三天。我把她帶到了下一個村子,給了村長一條毯子,讓他照顧她,并答應如果我回來的時候老太太還健康的話,就再給他一條。我記得,他對于我為了一條不值錢的老命而舍棄兩條毯子的做法感到非常驚訝。‘你為什么不把她留在灌木叢里?’他這樣問我。你看,那里的居民將適者生存這個道理發揮到了極致。
“離開老太太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碰到了那邊的這位朋友。”他朝著那個頭骨點了點頭;在寬寬的壁爐架的陰影中,獅頭似乎正居高臨下地沖著我們齜牙咧嘴地笑。“從黎明到上午11點鐘,我一直在趕路——趕了很長一段路,因為我想盡量多走一段。然后我把牛群放到草場上吃草,還派了跟車探路的土著小子去照看它們,打算到了傍晚六點的時候再次套車,趁著月光一直趕路到晚上十點。我爬進車里,一覺睡到了下午兩點半左右,便起來做了些肉,就著一小杯黑咖啡吃了晚飯;因為在那個時候,要弄到保鮮牛奶是相當困難的。就在我快吃完飯、那個叫湯姆的趕車人正在洗涮餐具的時候,這個小無賴趕著一頭牛回來了。
“‘其他的牛哪兒去了?’我問道。
“‘庫斯!’他說,‘庫斯(首領)!其他的牛都跑了。我一轉身的工夫,再回頭看,其他的牛就都不見了,只有“上尉”還在這兒,用它的后背蹭著一棵樹。’
“‘你是說你睡著了,讓它們都走散了,你這個混蛋!我要拿棍子抽你。’我生氣地說道,因為在這樣一個瘟熱傳播的地方要困上一周左右尋找牛群,這可不是什么讓人高興的事。‘你快去找,湯姆你也是,如果找不到牛群,你們就不要回來。我敢肯定,它們是沿著米德爾堡路往回走,現在一定走了有12英里遠了。你們倆什么話也別說,快去找吧。’
“趕車人湯姆罵了一通,又狠狠踢了那個小子一腳——那完全是他活該。接著,他用皮條把老‘上尉’拴在車轅子上,他們兩個就帶著長矛和棍子出發了。我本來也應該去的,但我清楚必須有人看著貨車,而且在夜里把車子留給他們兩個中的任何一個照管,我都不放心。事實上,我當時十分生氣,不過我對這種事早已經見怪不怪了。于是為了讓自己平靜下來,我就拿上一支打獵去了。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我四處尋找,結果也沒找到什么可以讓我開上一槍,但是最后,就在離貨車不到70碼的地方,我從一片合歡樹叢后面趕出了一只上了年紀的公黑斑羚。它徑直朝著貨車跑去。等它跑到離車幾英尺遠的地方時,我才有機會開槍射擊。我扣動,正中它的脊柱中央;它隨即跌倒,不再動彈,死得透透的。這一槍真是準極了,不過當然啦,這話不該由我來說。這個小插曲讓我的怒氣消了些,尤其是這只黑斑羚正好撞在貨車后部,所以我只需要將它的內臟掏出,用皮條綁住它的腿,把它拖上車就成了。等我做完這一切,太陽已經落山,一輪圓月當空升起,真是一輪美麗的月亮。之后在夜色尚淺時分,一份美好的靜謐籠罩了灌木林。這是在非洲灌木地帶間或會出現的景象。野獸不再游走,鳥兒不再啼叫。沒有一絲微風打擾寧靜的樹木,樹影不再搖曳,只是默默地拉長。但是,現在這一景象顯得既壓抑又荒涼,因為我完全看不到牛群和同伴的影子。我很感激老‘上尉’與我為伴;它正倚靠車轅子躺在那里,咀嚼著反芻的食物,神態悠閑。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上尉’開始變得焦躁不安起來。它先是鼻子呼哧呼哧地噴了陣氣,接著站起身來,又開始呼哧呼哧。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像個傻子一樣跳下貨車車廂四下察看,還以為是走失的牛群回來了。
“接下來的一瞬間我就后悔了,因為我突然聽到一聲咆哮,看到什么黃色的東西飛速閃過我身旁,落在了可憐的‘上尉’身上。牛兒痛苦地怒吼了一聲,接著是嘎吱一聲咬嚼,原來是一頭獅子一口咬在這只可憐畜生的脖子上。我這才明白發生了什么。在貨車里,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去取槍,于是我轉身一個箭步朝貨車奔去。我一只腳踩在了車輪上,想要翻身上車,但我整個人就像凝固了一般停在那里。原來,我正打算縱身一躍時,就聽見獅子在我身后,下一秒我就能感覺到這頭獅子,啊,那感覺真實得就像我能觸摸到這張桌子一樣。這么說吧,我能感覺到它正嗅著我垂下的左腿。
“哎呀!我當時的感覺真的很奇怪;我以前還從未有過這么奇怪的感覺。我嚇得一動都不敢動,而奇怪的是我好像對整條腿都失去了控制;它似乎有了自己的意志,想要一腳踢出去,就像人們在特別嚴肅的場合想要歇斯底里地大笑一樣。那頭獅子聞了又聞,從我的腳踝向上慢慢移動到了大腿處。我以為它要抓住我的腿,結果它沒有。它只是低聲地咆哮,又回到了牛的身邊。我稍微轉了轉腦袋,以便可以看見它的全貌。這大概是我見過的最大的一頭獅子——我見過的獅子要說也不少了,黑色的鬃毛濃密得驚人。你們可以看到它的牙齒是什么樣子的——看那里,很大的牙齒,不是嗎?總而言之,那真是一頭龐然大物。就在我四肢張開、躺在貨車的前轅桿上的時候,我突然想到,這頭獅子在籠子里看起來絕對會不同凡響。它站在可憐的‘上尉’的尸體旁,小心地取食它的內臟,嫻熟得像個屠夫。在這期間我一直不敢挪動,因為它舔食著那堆血肉模糊的碎肉的當兒,不停地抬起頭留意著我。等它把‘上尉’的肚子都掏干凈了,就張開嘴發出了一聲巨吼,不夸張地說,那聲音讓貨車都顫動了。緊接著就聽到另一聲咆哮在回應它。
“‘老天啊!’我想,‘它還有同伴。’
“這個念頭還沒有散去,我就看見一頭雌獅在月光下跳躍著穿過又高又密的草叢,在它身后跟著兩只獒犬大小的幼獅。它在我面前幾英尺處停了下來,搖擺著尾巴站在那兒,明亮的黃眼睛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可就在我以為一切都完了的時候,它轉身開始和幼獅啃食起‘上尉’來。就在離我還不到八英尺的地方,有四只獅子在咆哮著爭吵著,撕扯啃食可憐的‘上尉’的尸骨;我躺在那里,害怕得渾身一邊發抖,一邊冒著冷汗,就像被投入獅坑的但以理一樣。不一會兒,幼獅吃飽了,開始變得焦躁不安。其中一只繞到貨車后面,扯著掛在那里的公黑斑羚,另一只到了我的跟前,開始嗅聞我的腿。事實上,不僅如此,它還開始用粗糙的舌頭舔著我挽起的褲腿下露出的皮膚。從它舔的力氣越來越大和發出的咕嚕聲可以看出,它越舔越起勁。它銼刀般的舌頭即刻就要銼進我大腿的皮膚——幸好我皮糙肉厚——大腿就要流出血來,我想這下完了,這次可是沒法活命了。于是我就躺在那里,回憶我的罪過,并向上帝祈禱,心想無論如何,這輩子還算是沒有白活。
“突然間灌木叢中傳來了一陣嘩啦嘩啦的聲音,還夾雜著呼喊聲和口哨聲,原來是那兩個小子趕著牛群回來了。他們發現牛群的時候,這些牛正聚在一起往前走。幾頭獅子抬起頭,豎起耳朵聽著,然后就一聲不響地跑開了——我也昏倒了。
“那晚獅子沒有再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的神經算是平復了;但是一想到我在那四只獅子的爪下——或者毋寧說鼻下——的遭遇,還有我的公牛‘上尉’的悲慘命運,我就滿腔憤怒。我很愛‘上尉’這頭了不起的老牛。我氣得像個傻子一樣,打算去攻擊它們這一大家子。這是一個首次出獵的新手才會犯的錯誤,但我竟然還是去了。我吃了早飯,在那條被幼獅舔得劇痛的腿上擦了些油,就帶著趕車人湯姆出發了——他可一點兒也不喜歡這差事。我這次帶的是一支普通雙管12號滑膛槍,也是我的第一支后膛槍。我之所以帶上滑膛槍,是因為它能精準地射出;經驗告訴我,滑膛槍對付獅子和一樣有效。獅子是一種皮肉柔軟的動物,只要射中它的身體就不難解決了。相比較而言,射殺一只羚羊還要更費些周章。
“我們出發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獅群在白天的藏身之處。距離貨車300碼的地方是一處山岡,上面零零散散地圍了一圈合歡樹。穿過合歡樹,就是一片開闊的平原,一直延伸到一處幾近干涸的盆地,也可以說是個占地大約一英畝的水洼,密布著枯萎的黃色蘆葦葉。這處盆地的另一邊向上斜伸到一條溝壑的邊緣。溝壑原先由激流不斷沖刷形成,現在里面密密長著灌木叢,還有幾棵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大樹。
“我即刻想到,在這個干涸的盆地里很可能會找到我的這些朋友,因為沒有什么比躺在蘆葦中更讓一只獅子喜歡的了。這樣它既可以洞察周圍,而且自己也不會被發現。于是我決定前往一探究竟。就在我繞著盆地走到一半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只藍角馬的殘骸,很明顯是三四天之前被獅子獵殺的,一部分已經被獅群吞食;周圍的其他跡象讓我很快確信,就算獅群那一天不在這盆地里,它們也經常到這里來。但是如果它們在這里,問題在于怎么引它們出來;想要深入盆地去追蹤它們顯然是不可行的,除非是誰不想活了。此時,一陣大風從貨車的方向席卷而來,掠過整片蘆葦地,向灌木叢生的干溝吹去。我首先萌生了一個念頭,就是燒掉蘆葦叢,我之前提過那里很干燥。于是湯姆用火柴從蘆葦叢的左側開始點火,我從右側點火。但是蘆葦叢靠近根部的地方還是綠的,多虧借了風力,我們才點著了火。隨著太陽升高,風力也逐漸增強,蘆葦終于燒起來了。最終,大概過了半個小時,大火開始穩步地呈扇形向前推進,于是我繞到盆地另一邊視線開闊的地方等待獅群,一如我們今天站在矮林中射殺山鷸一樣。這樣做挺冒險的,但是當年我對自己的射擊充滿自信,并不在意這樣的危險。我剛到那里,就聽到了蘆葦叢被扒開的聲音,隨后一只動物就沖了上來。‘來吧。’我說。它來了。我能看到的只是一個黃色的物體,正準備射擊,突然發現躥出來的不是獅子,而是一只藏身在盆地中的美麗的小葦羚。這只小葦羚一定極易相信他人,才敢與獅群為鄰,就像上帝的羔羊,但我猜蘆葦叢一定很茂密,而且它與獅群保持了相當遠的一段距離。
“我放過了這只小葦羚,它就像一陣風一樣跑開了。我繼續盯著蘆葦叢。大火現在燃燒得像個熔爐;火苗噼里啪啦的,呼嘯著舔食蘆葦叢,向空中噴出的火焰有二十多英尺高,熱氣就像在火苗上舞蹈,令人頭暈目眩。但是蘆葦依然有一半是綠色的,大量濃煙生成,倚借風勢在低空像幕簾一樣向我席卷而來。此時,從火苗噼里啪啦燃燒的聲音中,我聽到一聲驚起的咆哮,接著一聲又一聲。現在可以斷定,獅群確實是待在窩里的了。
“我開始興奮起來,你們知道,除了受傷的水牛之外,沒有什么比一頭近距離的獅子更能刺激神經的了;當我透過濃煙看出獅群正活動在蘆葦叢的最邊緣,我變得更加亢奮。它們偶爾像兔子把腦袋伸出洞穴一樣探出頭來,看到我站在大約五十碼開外之后,又把頭縮了回去。我知道,它們身后一定越來越熱,所以這種狀態堅持不了多長時間。我想得沒錯,它們四只突然一起從藏身處沖了出來,那頭年老的黑鬃雄獅領先幾步。在我的經驗中從未看到如此壯觀的一幕:四只獅子飛躍著穿過草原,全身籠罩在濃濃的煙幕之中,身后是熔爐般熾熱燃燒的蘆葦叢。
“我估計它們是想跑到灌木叢生的溝谷之中,這樣就會在距我大約5到20碼處經過;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氣,舉起槍瞄準了那頭獅子的肩部——那頭黑鬃雄獅——這樣它在運動中向前一兩英寸,就能夠直擊它的心臟。來吧!我準備好了。我的手指正要扣動,但就在這時,我突然眼前一黑——有點兒蘆葦灰飄進了我的右眼。我跳起來揉搓著眼睛,等我終于睜開眼睛大致能看清楚的時候,最后一只獅子的尾巴恰好消失在了溝谷的灌木叢中。
“這個時候再沒有比我更要氣瘋的人了。太糟糕了,還是這樣一個在空曠地帶射擊的大好機會!然而,我沒有氣餒;我轉過身往溝谷方向走去。趕車人湯姆央求我別去了;按常理說我從不在膽量上逞強(我膽子也不大),但當時我下定決心,要么我殺死獅子,要么獅子殺死我。于是我告訴湯姆,如果他不愿意就不必跟著我了,但我一定要去;我的這位趕車人是個斯威士人[7],他們天生膽大,所以他只是聳了聳肩,一邊嘀嘀咕咕說我不是瘋了就是著魔了,一邊固執地跟隨我的腳步。
“不久我們就到了溝谷。這個溝谷大約300碼長,但樹木稀少;真正的刺激開始了。每一處灌木叢后都可能藏著一只獅子——這四只獅子肯定是藏在某個地方了,棘手的問題是,它們到底藏在哪兒。我四下察看,四處撥弄,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地方,心也提到了嗓子眼。終于,我得償所愿地瞥見一處灌木叢后有什么黃色的東西在移動。與此同時,從我對面的另一處灌木叢中跳出了一只小獅子,向燒盡蘆葦的盆地方向沖去。我迅速轉身,開槍射擊,它隨即一個跟頭栽倒在地,在離尾部兩英寸處折斷了背脊。它無助地倒在地上,只能怒視著我。湯姆隨后用長矛將它刺死了。我打開槍膛,快速抽出舊彈殼。事后想來,從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來判斷,我猜這彈殼已經炸開,并且留下了一部分布片在里。無論我怎樣試著裝進新的,都只能裝進一半;還有——你們相信嗎?——一定是被幼獅的呼叫招引而來,這時母獅現身了。它在離我20步左右的地方站著,擺動著尾巴,那樣子看上去要多兇惡有多兇惡。我慢慢向后挪步,想要推進新的,而它也跟著我小步子移動,每跑幾步就停下來弓起身子。危險迫在眉睫,還是推不進去。奇怪的是,我腦子里這時候想到的是那個制造的家伙——在這里就不說他的名字了——我真心希望如果獅子把我吃掉了,他會得到應有的懲罰。還是進不去,我試著抽出來,但也不行。如果合不上槍,就意味著我用不了另外那個,這就是把廢槍。我這就等于沒有槍了。此時,我一邊緊緊盯著母獅子,一邊向后退去,它正腹部貼地無聲無息地向前爬行,但還是擺動著尾巴瞪著我;從它的眼神中我知道再有幾秒鐘它就要撲過來了。我的手腕和手掌被的黃銅邊緣劃出了一道口子,鮮血直流——看,到今天還有傷疤呢!”
夸特梅因對著燈光舉起了他的右手,給我們看在手掌和手腕接合處留下的四五塊白色傷疤。
“但是那樣一丁點兒用也沒起。”他繼續說道,“紋絲不動。我希望再也不會有人遇到像我這樣糟糕的境況了。雌獅打起精神,我簡直陷入了絕境,就在這時,湯姆的喊聲從我身后傳來:
“‘你正在往那只受傷的獅崽那里去。朝右邊走。’
“盡管我腦子一片空白,還是聽懂了湯姆的話。于是我一邊像剛才那樣盯著母獅子,一邊轉向右邊繼續后退。
“讓我松了口氣的是,隨著一聲低沉的咆哮,母獅伸直了腰,轉過身去,朝溝谷另一頭飛奔而去。
“‘來啊,老大,’湯姆說,‘咱們回車子上去吧。’
“‘好的,湯姆,’我回答說,‘我殺掉其他三只獅子就回去。’因為這時候我已經下定決心要殺死它們,在我記憶里,之前或之后我都從來沒有這樣堅定地要做什么事。‘你想走的話就回去吧,或者在樹上待著也行。’
“他考慮了一下眼前的情況,然后就明智地爬到了樹上。我當時要是也爬上去就好了。
“這時,我找到了我的一把小刀,這把小刀帶有鉤子,于是我費盡周折終于把里殘余的舊彈殼布片掏了出來,就是這點破布幾乎要了我的命。它比一張郵票厚不了多少,絕對沒有一張書寫紙厚。掏出來之后,我給槍上了膛,在手腕和手掌接合處綁了條手帕來止血,就再次出發了。
“我剛才就看到那頭母獅跑進了一叢茂密的綠葉灌木之中——更確切地說是生長在水邊的好幾簇灌木;那兒有一條小溪順著溝谷往下淌,就在大約50碼遠的地方。我于是就往那里去。可是,等我到了那兒,我什么也看不到,于是我拾起一塊大石頭扔進了灌木叢中。我一定是砸中了另一只小獅子,因為它一下子就躥了出來,身子的一側暴露在我面前。我立刻抓住這個機會,一槍把它打死了。母獅這時也像一道閃電似的沖了出來。就在它沖出來的瞬間,我終于用另一發擊中它的肋骨,結果它像只被擊中的兔子一樣翻滾了三圈。我迅速又上了兩發,這時那只母獅又站了起來,前爪扒著地向我爬來,咆哮著、呻吟著,臉上充滿著我少有機會見到的惡魔般的憤怒。我又一次開槍,射穿了它的胸腔,它倒向一側死了。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時打死兩只獅子,我還從來沒有聽說其他人有過這樣的事跡。我自然很得意,于是又上了,繼續尋找那頭殺死‘上尉’的漂亮黑鬃雄獅。我小心翼翼地沿著溝谷慢慢往頂頭搜索,搜遍了沿路的每一簇灌木和草叢。這真是讓我興奮極了,因為我不能肯定哪一秒鐘它就會向我撲來。讓我稍稍感到寬心的是,我知道一頭獅子很少攻擊一個成年男子——我說‘很少’,是因為它有時候也會攻擊,你們一會兒就知道了——除非它陷入絕境或者受了傷。我大概找了它將近一個小時。有一次,在一簇須芒草叢中,我以為看到了點動靜,但是不能確定,等我踏進草叢時已經找不到它了。
“最后我到了溝谷盡頭,那里是條死路,一道50英尺高的石壁擋住去路。一條小瀑布順著石壁涓涓流下,而在石壁正前方大約70英尺處,是一個巨石堆,在它的縫隙和頂部生長著蕨類、雜草和矮小的灌木。巨石堆大約有25英尺高,兩側的谷壁也非常陡峭。我來到溝谷的頂頭,向四周望去,沒有那頭獅子的蹤跡。很顯然,要么是我在搜索的沿路錯過了它,要么是它早就逃跑了。我心里有點兒惱怒;但是晚餐之前憑著一人一槍解決了三只獅子也不賴啊,我有點得意忘形。于是我又往回走,繞過那四面無所依賴的卵石堆。這時我感到興奮勁兒已經過去,整個人都累壞了。而且,要把那三只獅子拖回去剝皮還要花更大的力氣。等我走過那個石堆——據我判斷大約有18碼的距離——時,我又回頭望了一眼。我眼睛很尖,但還是什么都沒看見。
“正在此時,我突然看到一個讓人寒毛直豎的場面。在卵石堆之上,那頭巨大的黑鬃雄獅正面對我站立著,它的輪廓在遠處崖壁的映襯下顯得格外清晰。它原來是趴伏在那里的,此時就像施了魔法一樣顯身了。它立在那里,尾巴不停地甩動著。它就像是諾森伯蘭府[8]大門口的獅像活轉了過來——我在哪里看到過那獅像的一張畫。但它沒有站許久。在我開火前——在我剛把槍抵住肩頭還沒來得及做什么的時候——它就向上徑直一躍,跳離了巖石,并且借著那有力的一躍劃過空中朝我飛撲過來。
“老天!它看上去真是一個龐然大物,令人敬畏!它高高地躍向空中,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就在它躍到最高點的時候我開槍了。我不敢再等了,因為我知道它都不用著地,會直接撲到我的身上。我甚至都沒有瞄準就開了這一槍,就像射殺一只沙錐一樣快速扣動。打中了,我清楚地聽見獅子挾著風聲呼嘯而來時,身體上砰地響了一聲。接下來的一秒我就被撲倒在地(幸運的是,我跌入了一處匍匐植物覆蓋的低矮灌木叢,這有效地緩解了沖擊),獅子撲在我身上,它的森森白牙咬上了我的大腿——我聽到牙齒與骨頭發出的摩擦聲。我痛苦地大喊,因為我一點也不像利文斯通博士[9]那樣,感覺到麻木或是快樂——順口提一下,我跟博士本人非常熟——我簡直就是做好了死的準備。然而,就在這一刻,獅子緊緊咬住我大腿的嘴突然松開了。它俯身瞧著我,身子來回搖擺,從它的血盆大口中鮮血直往下滴。它一聲咆哮,巖石都為之撼動。
“它來回搖動著,接著它巨大的腦袋重重砸在我的身上,我幾乎為之窒息。它就這樣死了。原來,我射出的那發正中它的胸膛,又從它背部中央的脊柱右側穿透皮肉而出。
“因為腿上傷口的疼痛,我才沒有昏厥過去。我一能夠喘上氣來,就設法拖著自己的身體從它身下移了出來。謝天謝地,它的大牙沒有把我的大腿骨完全咬斷,但我流了大量的血,如果不是湯姆及時趕到,把我手腕上的手帕解下系在我的大腿上,再用一根棍子將它擰緊,我想我就會失血過多而死了。
“對于我單槍匹馬獵殺一大家子獅子這樣的愚蠢行徑,這不啻一個公正的獎勵。真是千鈞一發。從那以后一直到我死的那天,我就是個瘸腿了;每到三月份,傷口總是疼得厲害,而且每三年還會有一次紅腫發炎。毋庸贅言,我在西庫庫尼國內沒有換到多少象牙。象牙落到了另一個人的手里——一個德國人——凈利賺了500英鎊。接下來一個月我都躺在床上,此后又一瘸一拐地過了六個月。現在,故事我已經告訴你們了,我可以喝口杜松子酒睡覺了。”
注釋
[1] 坦桑尼亞東北部一島。
[2] 西庫庫尼(Sikukuni,1814—1882),今南非境內東北部一地區巴佩迪人的國王。他于1861年即位。
[3] 南非東北部姆普馬蘭加省的一個城鎮。
[4] 南部非洲林波波河的一條支流,在今南非姆普馬蘭加省境內。
[5] 即東南部非洲的馬關巴部族(the Magwamba)。荷蘭殖民者因其出于裝飾目的的奇特鼻部畸形而以“疙瘩鼻”稱呼他們。
[6] 恰卡(T’Chaka,也稱為Shaka Zulu,約1787—約1828),非洲祖魯族首領,祖魯王國建立者。他被稱為軍事天才,但其殘酷統治也受到爭議。
[7] 斯威士人是東南非洲的一個民族,主要生活在今日的斯威士蘭和南非,還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莫桑比克。
[8] 諾森伯蘭府為倫敦一座詹姆斯一世時期的大宅,建于1605年,是諾森伯蘭公爵的府邸。它一直矗立在河岸街的最西頭,直到1874年被拆毀。
[9] 戴維·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英國探險家、傳教士,維多利亞瀑布和馬拉維湖的發現者,非洲探險的最偉大人物之一。他曾遭到獅子的襲擊,受了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