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老還童中英在線—返老還童中英在線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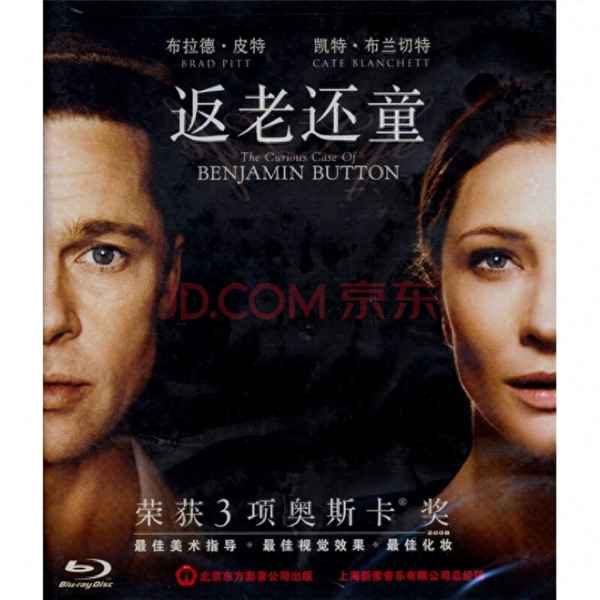
據說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從馬克·吐溫的一句話中獲得了寫作《返老還童》的靈感,那句話是這樣說的:遺憾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是在開始階段,而最糟糕的時光則是在結束階段。菲茨杰拉德只是把這句話在一個完全正常的人身上做了個試驗而已。但是,沒想到這篇故事寫成之后的幾個星期,他在塞繆爾·巴特勒的《札記》中發現了幾乎一模一樣的情節。
《返老還童》曾刊登在《科利爾》雙周刊上,不久菲茨杰拉德收到了一封瘋狂的讀者來信:“先生,我在《科利爾》雜志上看到了本杰明·巴頓的故事。我想說,作為一位短篇故事的作者,你會越寫越瘋的。我一生中見過許多人,但在我曾經見過的這些人當中,你是最了不起的。我本不想為你浪費筆墨,但是我愿意。”
我對菲茨杰拉德的本人的興趣遠遠大于對這篇小說的興趣。菲茨杰拉德一生創作了一百六十多部的短篇小說,涉獵各種題材。《返老還童》寫于1922年,屬于奇幻色彩小說,是他的小說狂想曲中的一部分。菲茨杰拉德是因為1920年春的小說《塵世樂園》一夜而紅的,隨后他就迎娶了美麗而瘋狂的新娘澤爾達。菲茨杰拉德出名后如此賣力的寫作,與他這位貌美狂野的新娘估計有很大關系,因為之前她就曾嫌棄他“錢途”黯淡而解除過婚約。1922年到1923年間,他正在構思長篇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但為了維持日益奢華的社交和生活,他寫了很多短篇小說給商業雜志,其中就包括《返老還童》還有《一顆像里茨飯店這么大的鉆石》。
1923年,他曾寫道:“去年冬天我不要命地工作,但寫出來的都是垃圾,這不僅損害了我的鋼鐵般的體格,還幾乎讓我心碎。”1937年,在另一篇回憶年輕時期的文章中,他又寫道:“涌入我腦海的所有故事都帶上了悲慘的色彩——我小說中的那些可愛的年輕人遭到了毀滅,我的短篇小說中的鉆石山被炸毀,我的百萬富翁像托馬斯·哈代的農民一樣美麗而悲慘。”提到這些早期作品的評價,我的意思并非說這些給商業雜志的小說寫的很爛,對于一個能寫出《了不起的蓋茨比》和《夜色溫柔》這樣的傳世之作的天才作家來說,他的任何作品都具有我們不可忽視的特質。對這些掩蓋在巨大榮耀下的作品,對這些為生活所迫的迅疾狀態下寫出的作品,也許,閱讀時有一顆理解的平常心會好很多。
《返老還童》這篇小說的創意是足夠新奇,至少發表時能足夠吸引大眾獵奇的眼球。但創意的過于新奇和故事之間的平淡無奇很容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落差,如何合理處理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讓讀者在一種驚駭之余不忘記思考和接納這種奇異事件就需要作者高超的敘事技巧和講述故事的能力。小說的開篇就位了本杰明·巴頓的出生鋪陳了很多細節,比如介紹當時的風俗,巴頓家族的名望,“羅杰·巴頓夫婦在南北戰爭的巴爾迪莫擁有顯赫的社會地位,而且非常富有”,因此之故,我們似乎預知到了本杰明出生之后的命運逆轉,為他一生的波折多難的經歷做好了陳述。
本杰明從出生時的老人,“是一個大約七十歲的男人;他洗漱的頭發全白了,從下巴垂下來的長長的煙灰色胡須,被窗外進來的微風吹得前后飄蕩”;到結尾時無意識的嬰兒,“他不記得了。他記不清最后一次喂他的牛奶是熱的還是冷的,以及日子是怎樣過去的”。從老人到嬰兒的經歷似乎也是一個記憶縮減,漸趨于無的過程。除此之外,本杰明與其他人的生活經歷都是一樣的,娶妻生子,戰爭,讀書……他的不同只在于逆時間經歷這一切。而這種記憶的逆轉所導致的不僅僅是人生的錯位,更是愛與錯的喪失。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篇小說的主題是永恒的喪失。當本杰明意識到他永遠跟不上他人生活的時候,他所保留的只能是自我的孤獨,虛無的影子。
小說的末尾部分中寫到了他的往事——圣·胡安山上的槍林彈雨;婚后幾年繁忙的夏日里,為了他深愛的年輕的希爾迪加整天工作至夜幕降臨;在那之前,與他祖父在蒙羅大街老巴頓的陰暗房子里坐著抽煙到深夜,“所有這些都像虛幻的夢一樣從他心中消失了,好像這些事從來沒有發生過”。真的是從來沒有發生過,本杰明注定無法在后來人的記憶中存留——除了在一篇虛構的作品中,才能以其真實的面目出現。讀這篇小說時,我一直再想如果是博爾赫斯處理這樣的題材的短篇一定會有所不同。當然,博爾赫斯是等不到這樣的機會了,看看大衛·芬奇在電影版的《返老還童》(又名《本杰明·巴頓奇事》)中處理起這樣的題材,也是得心應手,頗能領會菲茨杰拉德原著的精髓。
電影版《返老還童》中,當本杰明把自己越來越年輕的秘密有些得意地告訴幫他剪發的老婦人時,她卻告訴本杰明為他感到難過,因為“你要經歷所有愛你的人都比你先死去,這還真是一個不小的責任”。本杰明愣住了,因為他從來沒有用這種方式考慮過生與死的問題。老婦人看著變得有些沉重的本杰明,又告訴他說要坦然面對人生中的生與死,“我們注定要失去我們所愛的人,要不然我們怎么會知道他們對我們多么的重要?”
這只是其中打動的我的一個細節。其他的還有很多:開始逆時針行走的時鐘,被閃中七次的老人,黛西一系列的偶然發生的所引發的必然的車禍,憂傷無比的愛情……導演大衛·芬奇在影片中,細膩鋪陳的多個細節,讓這個本來改變自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說《返老還童》的故事具有了多重意義上的異樣神采。盡管菲茨杰拉德生前很看不起電影這種媒介形式,但如果不是因為這部電影,我想很難會注意到他眾多作品中的這一個小短篇。
菲茨杰拉德的另外一篇奇幻色彩的小說《鉆石》中,主人公昂格爾假期受邀去同學珀西家做客,至此進入了一個夢幻般的世界。珀西家住在一個神秘的從不為人所知的鉆石山中,昂格爾在那里見識領略到了什么是有錢人。具有黑色幽默的情節設置是,昂格爾沒意識到,從此他再也不能走出鉆石山了,除非被殺死,因為鉆石山的消息不能被外界所知。
菲茨杰拉德的幽默和諷刺的語言風格,以及對敘事出色的掌控能力,讓這篇小說具有了一種之前不具備的從容和坦率。我很驚訝他在書中對富人生活以及金錢的那種有些病態的癡迷的描述,但正如美國文學批評家迪克斯坦所言,菲茨杰拉德雖然著迷于富人的習慣和風尚,并為金錢所帶來的自由所吸引,他心里卻熱切地希望成為一名嚴肅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五十年后仍然能夠打動讀者,“在富人中間他從未忘記自己是個局外人,但他同時是個洞幽燭微而富有同情的觀察者。他留意到金錢能為富人購買的東西如此之多,但同時又如此之少——正如他后來發現的那樣,金錢為他們提供了自由和時尚,卻無法為他們消除失望和失落”。
是不是正因為這種失望的落差才讓菲茨杰拉德的這些奇幻和狂想故事的結尾都具有了一種悲劇性的內核?本杰明·巴頓悄無聲息地從世界的記憶中上消失了,“就好像從未發生過”。昂格爾從鉆石山中逃了出來,仿佛一場夢。現在夢醒了,繁華落幕,夜涼如水,沒有鉆石的光芒閃爍,只有黑夜依然照亮著黑夜。
(本文系出版的《返老還童》中英文對照譯本的序言)





